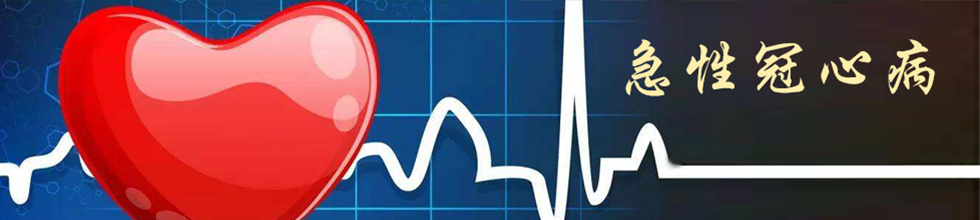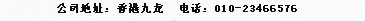苏合香丸与丝路医药文化交流医疗社会
苏合香丸与丝路医药文化交流
摘要:丝绸之路是古代外部世界同中国进行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一条主要通道。随着商业往来的持续与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域外医学知识和药物也进入中国,对中国医药发展产生重要推动性影响。苏合香在秦汉时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后,即被广泛应用于中原生活,后被医家作为药用。虽其使用方式、剂量以及主治疾病范围历经变迁,但至今仍是我国自主知识产权药品麝香保心丸的核心成分药物。本文拟通过详细梳理和阐述苏合香在中国医学中的药用演变历史,揭示丝绸之路在中外医药文化交流层面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对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丝绸之路中国医药发展苏合香丸演变史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商业贸易的纽带,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最耀眼的舞台。西汉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启了丝绸之路的新纪元,从此掀开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珠帘”,将中原与西域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此,各国军队、使者、商人、僧侣等人沿着这条道路来往络绎不绝。年,德国地理学家斐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vonRichthofen,-)在《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China:TheResultsofMyTravelsandtheStudiesBasedThereon)一书中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SilkRoad)。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发展,丝绸之路向西拓展到罗马,向东延伸至朝鲜半岛和日本,成为亚、欧、非各国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路。
香料自古以来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用途甚广,既可以作为香料熏染衣物居室,或者作为调料改善食物味道,也可以作为供奉神佛的圣物以及修身养性的雅物,还可以作为治病驱邪的灵药。香料产地多在西域,丝绸之路的开启为中原带来了品种繁多的域外香料,它们沿着陆地或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这些香料不仅丰富了中国上流阶层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对中国医药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很多香药至今仍然广泛应用于中医临床,其中苏合香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01苏合香的传入及其名称和用途考证(一)文学语境下的古代苏合香文化
汉代的丝绸之路主要出口丝绸、瓷器和茶叶等货物,换回西域的马匹、香料和毛毯等物品。汉乐府诗云:“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氍毹五木香,迷迭艾纳及都梁。”可见从西域运来的货物除氍毹等为毛织品外,其余均为香料。由于稀少难得,又因丝绸之路的路途遥远且艰险,所以西域香料在当时非常珍贵。
据文献记载,汉代对苏合香已有较多了解,达官贵人很早就发现西域香料的妙用,通过熏燃可以驱逐居室和衣物的异味。苏合香是较早传入中国的树脂类香料,一般做成香囊佩戴在身,往往人还未到,香气已悄然袭来,故深得文人雅士的追捧。西晋陆机作乐府诗《艳歌行》“被之用丹漆,熏用苏合香”,即描写了在居室里用苏合香熏香的情景。另据《班固与弟超书》云:“窦侍中令载杂彩七百匹、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氏马、苏合香。”记载了东汉权臣窦宪曾派遣专人到西域用丝织品交换马匹和苏合香的场景。
苏合香还可作为男女定情之信物,以寄托相思。西晋傅玄作《拟四愁诗》云:“佳人赠我苏合香,何以要之翠鸳鸯。”描写了缥缈弥漫的苏合香熏染佳人居所和衣物的场景,并与浓情蜜意的情愫连在一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上层社会也流行使用苏合香。南朝梁武帝萧衍作《河中之水歌》云:“十五嫁于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珊瑚挂镜烂生光,平头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嫁与东家王。”诗中描述了洛阳佳丽莫愁嫁卢家,闺房以兰馨雅洁桂木为梁,四处散发着郁金和苏合香的芬芳。梁简文帝萧纲作《药名诗》云:“烛映合欢被,帷飘苏合香。”梁孝元帝萧绎作《香炉铭》云:“苏合氤氲,非烟若云,时秾更薄,乍聚还分,火微难尽,风长易闻,孰云道力,慈悲所熏。”南朝梁吴均作《秦王卷衣》云:“玉检茱萸匣,金泥苏合香。”另有《行路难》云:“博山炉中百合香,郁金苏合及都梁。”南朝陈江总作《闺怨篇》云:“寂寂青楼大道边,纷纷白雪绮窗前。池上鸳鸯不独自,帐中苏合还空然。屏风有意障明月,灯火无情照独眠。辽西水冻春应少,蓟北鸿来路几千。愿君关山及早度,念妾桃李片时妍。”这些诗句描写的也都是苏合熏香的情景。由于苏合香来源有限,且香气高雅悠长,非寻常百姓家所有,尝为皇家贵族香炉熏燃。
及至唐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与西域诸国的贸易交往也更加频繁。苏合香渐渐深入民间巷陌,成为男女情意的载体。在《全唐诗》中就有很多描写苏合香的诗句,诸如“游童苏合带,倡女蒲葵扇”(李瑞《春游乐》)、“横垂宝幄同心结,半拂琼筵苏合香”(李白《捣衣篇》)、“霞衣最芬馥,苏合是灵香”(韦渠牟《步虚词》)、“胭脂含脸笑,苏合裛衣香”(白居易《裴常侍以题蔷薇架十八韵见示因广为三十韵以和之》)、“御气馨香苏合启,帘光浮动水精悬”(陈标《秦王卷衣》)等诗句,皆可见到苏合香的踪影。
此外,《舞曲口传》记载了印度阿育王曾患病,求苏合之药草,七日而得,病即痊愈,其臣乃以药草为甲胄而作苏合香舞。乐舞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唐代软舞中有《苏合香舞》。花树芳香,佳人舞姿婀娜,凝聚在诗词中。唐代吴少微作《古意》诗云:“洛阳芳树向春开,洛阳女儿平旦来。……北林朝日镜明光,南国微风苏合香。可怜窈窕女,不作邯郸娼。妙舞轻回拂长袖,高歌浩唱发清商。”由此可见,苏合香舞是一种长袖舞,通常伴以乐曲歌声。后由日本遣唐舞生和迩部嶋于—年传入日本。苏合香舞在中国虽已失传,在日本却广为流传。日本宫廷所藏《舞乐图》展现了舞者身穿宽大长袍、头戴苏合草叶踏歌而舞以祛除病邪的场景。在《信西古乐图》中也画着挥动长袖翩翩起舞的四名舞者。这些乐舞皆取材于唐代乐谱中的精华。由此可见,艺术的形成与流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合香的传播。
(二)苏合香的药名考证
苏合香为金缕梅科枫香属植物苏合香(LiquidambarorientalisMill)树干中渗出的香树脂,“苏合”二字是拉丁语storax的音译。苏合香树适宜生长于湿润肥沃的土壤,主要分布于印度、土耳其、埃及以及波斯湾邻近各国。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Hirth)认为最早的古代苏合产于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东南等地。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按郭义恭《广志》云:此香出苏合国,因以名之。”伊朗古称苏合国,由此可见苏合香因产地而得名。
苏合香的入药史最早可追溯到南朝梁陶弘景所著的《名医别录》,书中云:苏合香生中台川谷。恐失考,其后历代医家多有论述。苏合香,又名帝膏、苏合油、苏合香油、帝油流、咄鲁瑟剑。从上述数个“又名”可知这一药材的基本概况。后唐进士侯宁极在其所著《药谱》()中将苏合香称为“帝膏”。自从打通丝绸之路以来,凡外国使臣来中国朝见皇帝,贡品中就有苏合香,加之苏合香是一种黏稠的膏状物,故“帝膏”的名称既反映了药材的基本形态,也反映了其在皇宫中的使用情况。北宋地理学家乐史在其所著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中使用“苏合油”的名称,反映了苏合香是油脂类物品(详见下述)。其后宋代官方专门设立太平惠民局,将苏合香称为“苏合香油”,并指出有香气的是真品。年,叶橘泉先生在其所著《现代实用中药》中又将苏合香称为“帝油流”。而“咄鲁瑟剑”则是梵语sturuka的汉译名,多出自佛经。由于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故佛经中苏合香多为梵语音译。
(三)苏合香的传入及药材考证
关于苏合香药材在我国古代史书和本草文献中记载颇多。据文献记载,棪树胶可能是提炼苏合香的原料。《集韵》云:“棪,木名。胶可和香为苏合。”棪树胶为苏合香之说亦见于《异物志》和《类篇》等著作。
先秦旷世奇书《山海经》中有苏合香的相关记载,据此可推测苏合香在先秦时期传入中国。但《山海经》所载皆为虚幻的神话传说,且很多内容是两汉时期所补充,故将先秦作为苏合香传入中国的说法仍有待考证。《三国志》卷三十魏志注引曹魏郎中鱼豢所著《魏略·西戎传》中记载大秦物产,有“一微木、二苏合、狄提、迷迷(当为‘迷迭’)、兜纳、白附子、熏陆、郁金、芸胶、熏草木十二种香”。《太平御览》卷九百八十二引西晋郭义恭所著《广志》曰:“苏合香出大秦国,或云苏合国。国人采之,笮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贾客。或云合诸香草煎为苏合,非自然一种也。”大秦国即丝绸之路的终点古罗马帝国。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BertholdLaufer)在《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ChineseContributionstotheHistoryofCivilizationinAncientIranwithSpecialReferencetotheHistoryofCultivatedPlantsandProducts)中指出苏合香经波斯传入印度,然后经丝绸之路再传入中国,前述“苏合香舞”在唐代由印度传入中国也印证了这种说法。在梵语中,rasamala(英文为altingiaexcelsa,即东印度苏合香树)的意思为粪便,这个字被爪哇人和马来人采用作为苏合的名称,可能是针对苏合的颜色而言,类似中国“狮子屎”的说法(详见下述)。由此可见,西亚和印度很早就有香料贸易。
南朝宋范晔编撰了我国第一部香类专著《和香方》(刊于年),序云:“甘松、苏合、安息、郁金、柰多、和罗之属,并被珍于外国,无取于中土。”随后在所著《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云:“西域出诸香、石蜜。苏合香出大秦国……合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广志》也有类似记载:“或云合诸香草煎为苏合,非自然一种物也。”《魏书》卷一百二《西域传》记载,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土地平正,出熏陆、郁金、苏合、青木等香”。《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载,扶南国于天监“十八年,复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罗树叶,并献火齐珠、郁金、苏合等香”;在中天竺国条记载:“其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玑、琅玕、郁金、苏合。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采苏合香,先煎其汁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是以展转来达中国者,不大香也。然则广南货者,其经煎煮之余乎?今用如膏油者,乃合治成者尔。无滓者为上。”由此可见,苏合香从状态上看为近油汁状香膏,气味香浓;贩来中国的多为胶滓,质坚味淡。那时候从丝绸之路运送物品动辄需要耗费半年以上时间,加之西域地理及气候条件又恶劣,油汁状的苏合香膏要求的保存条件可能会高一些。如果直接带的是渣滓,那么装在袋子里就可运输,由于中原不产苏合,所以只要到达中原即可卖得高价。陶弘景所著《本草经集注》:“(苏合)俗传云是师子屎,外国说不尔。今皆从西域来,真者虽别,亦不复入药,唯供合好香尔。”明代朱橚等人所著《普济方》卷二百三十九《诸虫门·诸虫附论》也有“破宿血杀虫,以狮子屎(即苏合香)服之”的记载。北宋唐慎微所著《证类本草》云:“狮子屎是西国草木皮汁所为,胡人将来,欲贵重之,饰其名尔。”这似乎解释了陶弘景的“狮子屎”说法,即苏合香是一种煎草木皮汁而制成的复合香,颜色赤黑,貌似狮子屎。
唐代苏敬等人编纂的《新修本草》云:“(苏合香)从西域及昆仑来。紫赤色,与紫、真檀相似,坚实极芬香,惟重如石,烧之灰白者好。云是师子屎,此是胡人诳言,陶不悟之。犹以为疑也。”唐代陈藏器云:“按师子屎,赤黑色,烧之去鬼气,服之破宿血,杀虫。苏合香,色黄白,二物相似而不同。”由此可见,陶弘景称狮子屎是苏合香的异名,苏敬认为称狮子屎是以讹传讹,陈藏器指出二者不同,认为“苏合香色黄白”与赤黑色的狮子屎相似而不同,狮子屎极臭。
北宋叶廷珪所著《名香谱》云:“苏合香油出大食国,气味皆类笃耨香。”北宋苏颂编撰的《本草图经》云:“药中但用如膏油者,极芬烈。”沈括所著《梦溪笔谈》云:“今之苏合香,如坚木,赤色。又有苏合油,如粝胶,今多用此为苏合香。按刘梦得《传信方》用苏合香云:皮薄,子如金色,按之即小,放之即起,良久不定如虫动,气烈者佳也。如此则全非今所用者,更当精考之。”明代陈嘉谟所著《本草蒙筌》云:“(苏合香)来从西域,卖自广东。气极芬香,色乃紫赤。或云系诸香汁,煎合成就。一说是狮子屎,故饰其名。”李时珍曰:“按《寰宇志》云:苏合油出安南、三佛齐诸番国。树生膏,可为药,以浓而无滓者为上。”从上述记载可知,苏合香是由西亚、中亚、东南亚经陆地或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且在当时发现已有次品出现。按《新修本草》所云“与紫真檀相似,坚实”者;《梦溪笔谈》所云“如坚木,赤色”者,以及《本草图经》所云“今广州虽有苏合香,但类苏木,无香气”者,均不是苏合香的正品。
从魏晋到明代,关于苏合香颜色和药材形态的记载众说纷纭。苏合香有固体之丸状,也有液体之油露。丸状者系煮煎香料之后所余渣滓之团块状凝结物,即苏合香丸。《旧五代史》卷五十八《崔协传》,后唐明宗不用李琪而任崔协为相,任圜陈奏,请命琪为相:“舍琪而相协,如弃苏合之丸,取蛣蜣之转也。”液体之苏合香为油质,称苏合油,明代又称苏合香油。唐代刘禹锡著《传信方》所言按之即少且色黄的苏合香是从香树中自溢外出的苏合香;沈括所言状如“粝胶”的苏合香实际上是苏合油;而用树皮煎煮而得到的苏合香则如坚木,色赤,香味不浓。大体来讲,唐代之前多用粗制苏合香;唐代之后,特别是宋代以来多用精制苏合油,这也与当时的制药工艺有关。美国汉学家谢弗(EdwardH.Schafer)也认为苏合香是一种西域的树脂,在唐代以前的苏合颜色紫赤,即所谓“狮子屎”;而唐代的苏合是用来制作香膏的马来枞胶。此书又翻译为《唐代的外来文明》。北宋之后药用的苏合香一般是苏合油,是半凝固状的胶体。《元史》卷二百九《安南传》载,世祖中统三年诏,要求安南国自次年始,“每三年一贡,可选儒士、医人及通阴阳卜筮、诸色人匠,各三人,及苏合油、光香、金、银、朱砂、沉香、檀香、犀角、玳瑁、珍珠、象牙、绵、白磁盏等物同至”。《明史》卷三百二十《外国之朝鲜传》,载永乐元年四月,“复遣陪臣李贵龄入贡,奏芳远父有疾,需龙脑、沉香、苏合香油诸物,赍布求市。医院赐之,还其布”。
(四)苏合香的药用价值考证
苏合香在西域诸国一般只作外用,多不口服。但是传入中原后,苏合香与中原文化相融合,渐渐由神飨转为人用,由外用转为内服,由单味向复方发展。唐代是中外文化交流非常活跃的时期,从敦煌等地出土的医学文献以及《千金方》《外台秘要》等古代医书来看,印度吠陀医学对唐代医学的影响较大。香药曾被用于佛教祭祀活动,苏合香被列为香中上品,视为“四香”之一。内服苏合香则寄寓着古人梦想服食香药以求长生不老的美好愿望,希望通过服用神佛飨用之物而获得神佛一样的生活。由此可见,通过丝绸之路而来的苏合香等香药的流传与佛教的传入有一定的关系。
据文献记载,苏合香在汉晋时期既可外用辟邪,又能作为药物口服;既可单独使用,也可与其他药物组成复方药剂。陶弘景所著《名医别录》将苏合香列为上品:“味甘,温,无毒。主辟恶,杀鬼精物,温疟,蛊毒,痫痓,去三虫,除邪,不梦忤魇,通神明。久服轻身长年。”这是关于苏合香药用的较早记载。医家认为苏合香既能治病,也可养生。然而,苏合香虽有“轻身长年”的功效,但是由于当时次品盛行而致真假难辨,陶氏曾主张苏合香只供合好香用,不宜入药。姚思廉所著《梁书·诸夷传》中也有记载“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对开窍醒脑有奇效,又能清热止痛,可作外敷药。但《梁书》曾论及真假苏合香的困惑,认为经商贾辗转来中国之苏合香多为次品“不大香也”;而西域进贡的苏合香则为真品,唯帝王可享用无虞。《补辑肘后方》卷四治卒大腹水病方:“真苏合香、水银、白粉等分。蜜丸,服如大豆二丸,日三,当下水。节饮,好自养。”这是关于苏合香较早的复方制剂,但方中的药物种类还比较少。
由此可见,苏合香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原后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历代医家结合中医传统理论对此多有发挥,并积累了丰富的用药经验。宋代还有一种苏合香酒盛行于世,沈括所著《梦溪笔谈》曰:“苏合香酒,极能调五脏,治疾有殊效。”南宋赵汝适所著《诸蕃志》卷下记载:“苏合香油出大食国,气味大抵类笃耨,以浓而无滓为上,番人多用以涂身。闽人患大风者亦仿之。可合软香及入医用。”明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云:“苏合香,气香窜,能通诸窍脏腑,故其功能辟一切不正之气。”清代张璐在《本经逢原》中进一步阐明:“苏合香,聚诸香之气而成,能透诸窍脏,辟一切不正之气,凡痰积气厥,必先以此开导,治痰以理气为本也。凡山岚湿之气袭于经络,拘急弛缓不均者,非此不能除。但性燥气窜,阴虚多火人禁用。”医家还常常针对不同病症与不同药物配伍使用:猝然昏倒、不省人事的寒闭症,常配麝香、丁香、安息香等;胸腹疼痛之症常与石菖蒲、半夏、藿香同用;胸痹心痛之症常配檀香、冰片、乳香等制成丸剂,如苏合香丸。
视死如生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特征。苏合香,不仅生者用之,而且死者墓中亦可见到。三国史料就有以香料置于棺椁中防腐的零星记载。唐代欧阳询所著《艺文类聚》卷四十礼部下《冢墓·从征记》曰:“刘表冢在高平郡。表子琮捣四方珍香数十石著棺中,苏合消救之香,莫不毕备。永嘉中,郡人衡熙发其墓,表貌如生,香闻数十里。熙惧,不敢犯。”由此可见,在三国时期,我国就已经知晓苏合香等香药可以防腐。直到宋元时期,以香药置棺防腐在敦煌沙洲等地渐成风俗。《马可·波罗游记》曾记载,尸体入殓棺内之后要“撒上大量的香树胶、樟脑和其他药物”,反映出当时的尸体装殓十分注意防腐措施。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苏合香内服具有抗血小板聚集、扩张冠状动脉、抗心肌缺血、祛痰、抑菌、抗炎等作用,外用可以杀菌消毒、缓解炎症,并能促进溃疡与创伤的愈合。临床上可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流行性乙型脑炎、一氧化碳中毒后遗症、各种呼吸道感染、呃逆等疾病。随着现代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苏合香的用途也在不断拓展,可以造福更多的患者。
02苏合香丸的古今变迁与中西方医药文化交流(一)吃力伽丸与苏合香丸的传承关系
从现存古代文献考证,“苏合香丸”的名称可追溯自《广济方》。五代史学家刘昫编纂的《旧唐书·玄宗本纪》云:“开元十一年九月己巳,颁上撰《广济方》于天下。”《广济方》是由唐朝政府颁布的官修方书,编撰目的据《刊广济方诏》云:“(朕)犹虑单贫之家,未能缮写,闾阎之内,或有不知。倘医疗失时,因致横夭,性命之际,宁忘恻隐。宜令郡县长官,就《广济方》中逐要者,于大板上件录。”本书颁行后,广济民众,传习甚广,成为唐代医者及民众习用的方剂手册,并流传到日本等国。可惜在经历千般劫难后,此书终未能传世。但是唐代诸多著名方书,如《千金方》《外台秘要》等均将《广济方》列为主要参考书籍,对其方剂予以吸收和利用,《广济方》的内容也因之得以保存。
“吃力伽”是白术的梵语音译,西晋嵇含所撰《南方草木状》(刊于年)始录此名,在卷上草类收载:“药有吃力伽,术也。”并且在所附图中注明:“吃力伽一名术,有白术、苍术、云头术数种。”该书记载了广东、广西等地的南方药用植物。可见《广济方》所用“吃力伽”的名称与《南方草木状》有一定关系。唐代王焘所著《外台秘要》(刊于年)转引《广济方》中的“吃力伽丸”方时也指出:“吃力伽,白术是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十二草部曰:“术,西域谓之吃力伽,故《外台秘要》有吃力伽散。扬州之域多种白术,其状如枹,故有杨桴及桴蓟之名,今人谓之吴术是也。”据此可推知,将“白术”称为“吃力伽”可能是地方的俗称。
《外台秘要》还详细转录了“吃力伽丸”所含的药物名称、用量、制法和服用方法,并指出吃力伽丸可用于治疗“传尸骨蒸,殗殜肺痿,疰忤鬼气,卒心痛,霍乱吐痢,时气鬼魅,瘴疟,赤白暴痢,瘀血月闭,痃癖疔肿,惊痫,鬼忤中人,吐乳狐魅”等病症。另据《外台秘要》载,可将吃力伽丸“蜡纸裹绯袋盛,当心带之。一切邪鬼不敢近”,可见将其佩戴在身可辟邪鬼。“腊月合之有神,藏于密器中,勿令泄气出,秘之。”古人将合药时间选在鬼神聚集的腊月,可见其有辟邪镇鬼之功用。
唐代是丝绸之路沿途贸易活动的鼎盛时期,香药贸易也出现了高潮。唐代开元年间“吃力伽丸”曾作为宫廷赐药,盛行一时。李林甫的书记苑咸在《为李林甫谢腊日赐药等状》中记载:“昨晚内使曹侍仙至,奉宣圣旨,赐臣腊日所合通中散、驻颜面脂及钿合,并吃力伽丸、白黑蒺藜煎、揩齿药等。”腊日俗称“腊八”,相传为释迦牟尼成道日,显然这种赏赐彰显了吃力伽丸的佛教意义。吃力伽丸以梵语音译名作为方名,且方中多用诃黎勒、荜茇、龙脑等印度香药,故可判断其为古印度药方。此外,吃力伽丸中包括多种香药,服用亦可清新口气、提神醒目。唐代医家以西域香药为主组成药方,并借佛教梵语命名,反映了唐代西域香药随佛教传入中原后的广泛使用。
日本著名汉方医学家丹波元坚所著《杂病广要·中风门》在论及“苏合香丸”时注曰:“此方本出《广济方》,谓之白术丸,后人编入《外台》。”从中也可看出吃力伽丸的出处以及与苏合香丸的传承关系。
(二)苏合香丸在中医中药的临证探析
丹波元坚之兄丹波元胤所著《中国医籍考》卷四十五《方论二十三》在论及《钱氏箧中方》时曾引文:“彭乘曰:钱文僖公集箧中方。苏合香丸注云:此药本出禁中,祥符中尝赐近臣。”祥符是宋真宗赵恒的年号,由此可知,“苏合香丸”名称的出现早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下文简称《局方》)。据沈括《梦溪笔谈》卷九记载,苏合香丸本在皇宫流传,为皇室御药。后至宋真宗时,太尉“王文正气羸多病,真宗面赐药酒一瓶,令空腹饮之,可以和气血,辟外邪。文正饮之,大觉安健,因对称谢。上曰:‘此苏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苏合香丸一两同煮,极能调五脏,却腹中诸疾,每冒寒,夙兴饮一杯。’因各出数榼赐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效为之,苏合香丸盛行于世”。当时用于煮酒的就是苏合香丸。从彭乘的叙述可知苏合香丸在皇宫中率先应用,再赐近臣,因治病有殊效而在民间传开,官员百姓仿效制作应用。
苏合香丸在宋代的盛行,并不仅唯宋真宗推崇,也因此方剂确有疗效。《苏沈内翰良方》记载:“予所亲见者,尝有淮南监司官谢执方,因呕血甚久,遂奄奄而绝,羸败已久,手足都冷,鼻息皆绝,计无所出,唯研苏合香丸灌之,尽半两遂苏。”现传《苏沈内翰良方》包括沈括和苏轼的医药著述,其中“苏合香丸”出自“沈方”,而沈氏《良方》据考应在宋哲宗赵煦绍圣二年()前成书,确切年代虽有待考证,但可知早于《局方》。
太平惠民局设立的初衷是因当时假药泛滥,药商重利轻义,人民生命安全难以保障,政府为提高药物专营水平而设。熙宁九年(),宋神宗赵顼在都城汴京设置太医局熟药所。崇宁二年(),宋徽宗赵佶在熟药所的基础上扩建成七个药局,由和剂局负责制药,供给惠民局出售。政和四年(),徽宗诏令减药价,将惠民局更名为医药惠民局,将和剂局更名为医药和剂局。后来又经过一系列改革,绍兴六年()南宋高宗赵构于临安设熟药所四处,绍兴十八年()改熟药所为“太平惠民局”。《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历经《太医局方》《和剂局方》的过渡以及太平惠民局形成的变革,于年定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并作为药局的制剂规范。南宋理宗赵昀宝庆年间(—)及淳祐年间(—)分别再予增订后成为目前流传的版本,全书10卷,共收方剂首。版本规范,校正明确,故研究苏合香丸时常选用《局方》。
“吃力伽”是梵语音译,听起来怪异,念起来也拗口。因此,《局方》在收载此方时将“吃力伽丸”更名为“苏合香丸”。不仅对药名做了更改,方中的药量也做了大幅调整。调整后的苏合香丸,虽然药物组成、功效主治与“吃力伽丸”相同,但是药名和药量均已改变。所以,苏合香丸据考最早应源于《局方》。从吃力伽丸与苏合香丸的对比可见,苏合香丸对于芳香药物的制药工艺更加细腻。不同于吃力伽丸仅将所有药物“捣筛极细”后制作蜜丸,苏合香丸在运用安息香时提出“别为末,用无灰酒一升熬膏”,冰片、苏合香要“入安息香膏内”,乳香要“别研一两”,香附要“炒去毛”,这些均体现了宋代应用香药的技术进步。
苏合香丸的组方理论最早可追溯到《黄帝内经》。《素问·脏气法时论》云,“心病者,胸中痛,胁支满,胁下痛,膺背肩甲间痛,两臂内痛”,并提出“芳香温通”的治法治则,“痛痹心痛,有寒故痛”,“温则消而去之”。从宋代开始,苏合香丸一直作为“芳香温通”的代表药物,主要功效是芳香开窍、行气止痛,常用来治疗寒凝气滞所致胸痹心痛,痰迷心窍所致痰厥昏迷、中风偏瘫,以及中暑、心胃气痛等病症,还可用于治疗外伤所致昏厥。南宋法医学家宋慈在《洗冤集录》五十二《救死方》曰:“卒暴、堕、筑倒及鬼魇死,若肉未冷,急以酒调苏合香圆灌入口,若下喉去,可活。”可见苏合香丸可用于昏厥等病的急救。由此推知,皇帝的推崇与赏赐、臣民的效仿与传播是苏合香丸盛行的主要原因,而疗效确切与功效显著是其盛行的根本原因。
自宋代以后,大量病例证明了苏合香丸的神奇疗效,其被奉为“圣药”,医家广泛将其用于胸痹、心痛、卒中、昏厥等病症的治疗,在元明清医学典籍中均可见其身影。元代危亦林所著《世医得效方》也曾提到用苏合香丸治疗卒暴心痛。直到今天,苏合香丸仍是中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等病症的主要药物。
宋元时期,滥用香燥药物之流弊显现。元代滋阴派朱丹溪(名震亨)就反对滥用香药,并提到产生的不良后果,在其所著《局方发挥》中指出:“苏合香丸用药一十五味,除白术、朱砂、诃子共六两,其余一十二味共二十一两,皆是性急轻窜之剂。往往用之于气病与暴仆昏昧之人,其冲突经络、漂荡气血,若摧枯拉朽然。”清代吴仪洛在所著《本草从新》云:“今人滥用苏合丸,不知诸香走散真气,每见服之,轻病致重,重病即死。唯气体壮实者,庶可暂服一二丸。否则当深戒也。”由此可见,凡以虚证为主或气血有损之症均不宜用芳香走窜之药,恐伤气阴。故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云:“(《局方》)盛行于金元,至震亨《局方发挥》出,而医学始一变也。”
此外,苏合香丸还可用于除疫辟邪宋慈在所著《洗冤集录》五十一《辟秽方》中曾提到:“苏合香丸,每一丸含化,尤能辟恶。”这可能与作者验尸的职业性质有一定关系,对于法医而言,防疫先行尤为重要。
至明英宗正统十年(),苏合香丸的组方被朝鲜金礼蒙等人编撰的《医方类聚》收录,苏合香丸的方剂远传至朝鲜。后来《医方类聚》又辗转流传到日本,同时也将苏合香丸的组方带到了日本,对两地汉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后来生产的治疗胸痹心痛的汉方制剂“救心丹”,其组方思路就源于中国的苏合香丸。
在清代的宫廷御方中也收载了“苏合香丸”,只是相比《局方》所载药量均减半,且删去薰陆香,并以木香易青木香,故药性相对平和。慈禧晚年曾患消渴、肝郁等症,年又患面瘫,当时太医开列的处方是“苏合香丸1料”,以期用辛香走窜之性,宣气通络,对气滞血瘀、络阻窍闭之证有效。《清宫医案集成》还收录一剂专为慈禧而设的美容护发方,名曰“香发散”,先将诸药细末,再用苏合香油搅拌,晒干研成细面,使用时将药粉掺匀于发上,后用密梳篦去,有去污香发,发落重生的功效。
(三)苏合香丸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和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苏合香丸的广泛应用,人们发现苏合香丸存在药丸较大、价格偏贵、服用不便等不足,在临床应用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年,在上海市卫生局的带领下,医院、医院、上海市心血管研究所、上海中药制药一厂等科研、医疗、生产单位组成了专门的科研攻关组,研发治疗冠心病的新型中成药。在唐代“吃力伽丸”和宋代“苏合香丸”的组方基础上,对苏合香丸所含的15种药材进行药理研究,结果发现苏合香脂和冰片是起主要作用的成分。又因龙脑、麝香、安息香、沉香等药材存在药源少、价格高的问题,不能满足广大患者的需要,因此精减原方删去一些贵重稀少的药材,改制成由5种药材组成的“冠心苏合丸”,用来治疗心绞痛属痰浊气滞者,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也是对古方苏合香丸推陈出新的一次成功尝试。但是其中仍然含有朱砂(硫化汞)和青木香(含马兜铃酸),而汞可导致体内重金属蓄积,马兜铃酸则对肾脏有毒性。
随后伴随制药工业的迅速发展,滴丸剂逐步被运用到中药制剂中。为了进一步改进处方和剂型,从而达到提高疗效、节约药材、改进质量的目的,年,由上海中药制药一厂、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药品检验所、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等单位组成协作组,开展对冠心苏合丸组成、药理、剂型和质量等方面的深入研究。经过反复试验,从冠心苏合丸中删去檀香、青木香、乳香、朱砂等4种药材,同时将苏合香的用量减半,并采用固体分散技术研制出“苏冰滴丸”。经过理化及生物有效性实验发现,与冠心苏合丸相比,苏冰滴丸具有体积小、崩解速度和溶出速度快、颗粒度细、起效快、疗效好等优点,同时在药方中去除了朱砂和青木香等有害成分。
随着苏冰滴丸在临床的广泛应用,人们又发现苏冰滴丸中仅含苏合香脂和冰片,由于冰片的含量高,对胃肠道刺激作用较为明显,且滴丸制剂的质量也不稳定,存在天热易粘连、冰片易析出等缺点,限制了其在临床的广泛应用。年,上海中药制药一厂又通过反复试验研究,在冠心苏合丸和苏冰滴丸的基础上添加了人参、丹参、麝香等中药材研制出“人参苏合香丸”。后来经过临床研究,发现人参苏合香丸虽然治疗效果有所提高,但是存在起效慢、组方偏热、价格偏高等缺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在临床的广泛应用。
年,由医院戴瑞鸿教授牵头的科研攻关小组,对苏合香丸的组方和剂型进行优化改良,保留了其中具有心血管活性的中药成分,去除了青木香和朱砂等毒性成分,增加了人参等补益成分,从而优化确定了7种中药组方和含量,并且采用了独特的微粒丸技术,成功研制出“麝香保心丸”。通过大量基础和临床研究,证实了麝香保心丸具有扩张冠状动脉、保护血管、抑制炎症、稳定易损斑块等作用机制,以及独特的促进治疗性血管新生作用,具有快速缓解症状和有效改善预后的临床效果,可以减少远期心血管事件。年,麝香保心丸获得首届“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奖”,并被认定为国家中药保密品种,处方和生产工艺受到国家保护。年1月,世界权威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在中医药专刊对麝香保心丸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专题报道,表明中医中药受到全球学界的广泛
转载请注明:http://www.jiajiasport.net/gxblyf/10843.html
- 没有推荐文章
- 没有热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