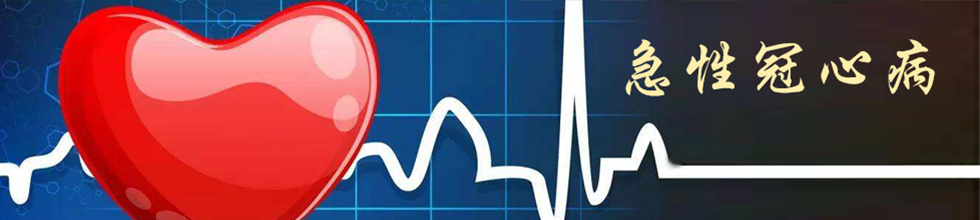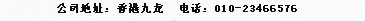新药故事从胆固醇假说到他汀的大规模应用
近年来,胆固醇的名声是越来越坏了。高胆固醇已经成了亚健康的代名词。超市的货架上摆满了印着“不含胆固醇”字样的各种食品,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高密度”与“低密度”的区别:前者是“好”胆固醇,而后者是“坏”胆固醇,越少越好。其实,这对胆固醇来说挺冤枉的。
相传,这个现在家喻户晓的油脂性化学物质最早是由法国化学家塞尔(Salle)在年从胆石(Gallstones)中发现的,但是到了年才有正式的文献记载,被法国化学家谢瑞尔(Chevreul)命名为“胆固醇”。胆固醇是哺乳类动物细胞膜的基本结构单元之一,对细胞膜的通透性和流动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胆固醇也是生物合成各种甾体类激素、胆汁酸(Bileacids)以及维生素D的前体。人体内胆固醇相对含量最高的器官是大脑,传递信息的神经细胞膜的结构与功能都与胆固醇密切相关。毫不夸张地讲,胆固醇是人和动物体内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化学物质。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成年人体内胆固醇的总量在35克左右,分外源性和内源性两种。外源性胆固醇来自食物,每天的摄入量一般在毫克~毫克(素食者低于此量);内源性胆固醇则是在肝脏中生物合成,每天大约有毫克。
食物里的胆固醇一般不容易被吸收,即便有少量被吸收了,它还是会对内源性胆固醇的生物合成产生抑制作用,从而维持体内胆固醇总量的相对稳定,所以从食物中摄取的胆固醇对人体内胆固醇的总量以及血液里的游离胆固醇浓度的影响都不大,这就是调节饮食对降低胆固醇的作用一般都不大的原因。胆固醇与冠状动脉硬化和瘀塞之间的联系很早就引起了医学界的注意,年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Virchow)就提出了冠心病的“胆固醇假说”(Cholesterolhypothesis)。根据病理解剖的发现,魏尔啸认为血液里的游离胆固醇在动脉血管壁上的沉积是造成动脉血管硬化和冠心病的直接原因。
这是一个超越时代的大胆假设,一直到年后的年,默沙东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从酵母菌的提取物中分离出了羟甲戊酸(Mevalonicacid),随后又证实了甲羟戊酸是胆固醇生物合成的中间产物,基础医学对于胆固醇代谢和调控的研究才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其后的几十年间,人们对胆固醇的生物合成和转移的研究,对摄入胆固醇的吸收和代谢的认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胆固醇与冠心病之间的联系也从一个原始的假说逐步上升为医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
远藤章咬定青山年,德国马普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了在胆固醇生物合成中起重要作用的物质——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HMG—CoAreductase)。内源性胆固醇是在肝脏中由乙酸经26步酶催化的生物反应合成的,其决速步骤就是由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催化的,从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HMG—CoA)到甲羟戊酸根(Mevalonate)的转化。当外源性胆固醇降低时,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的表达和活性就会增强,在肝脏内合成更多的内源性胆固醇,以弥补不足。可见要降低血液里的胆固醇含量,单靠改变饮食结构、降低摄入量是不够的。于是,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开始积极地寻找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的抑制剂。
到哪里去找这种酶的抑制剂呢?
日本生物化学家远藤章(AkiraEndo)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在自然界里,有很多微生物的生长是依赖于胆固醇和类萜化合物的。对于这类微生物来说,胆固醇的生物合成是它们的生命线,而抑制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的活性对它们则是致命的。远藤认为,自然界里一定存在着另一些微生物,它们在生存竞争中以抑制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的活性为目标,用“化学武器”去攻击那些依赖胆固醇的微生物,成为它们的克星,而这种“化学武器”很有可能就是天然的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大自然无奇不有,我们应该从哪里下手呢?抱着这个坚定的信念,凭借他和同行们对于不同微生物的充分了解,远藤领导日本三共制药公司的团队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辛辛苦苦地筛选了多种不同的微生物。
年,他们终于从桔青霉菌(Penicilliumcitrinum)中找到了第一个天然的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美伐他汀。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是人类征服其“第一杀手”冠心病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远藤章因此获得了6年日本国际奖[插图]和8年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
远藤章三共团队的新发现引起了制药界同行的极大兴趣,寻找天然的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立刻成了新药研发的大热门。年,默沙东实验室的科研团队依样画葫芦,在筛选了多个发酵提取物的样品后,从土曲霉菌(Aspergillusterreus)中分离出了一个几乎与美伐他汀完全一样的天然产物——洛伐他汀。两者唯一的区别是,洛伐他汀的3号位上多了一个甲基。不难想象,与美伐他汀一样,洛伐他汀也是一个高效的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
经过临床前的药效研究(Efficacystudy)和安全评估之后,三共制药率先开始了美伐他汀的临床试验,默沙东的洛伐他汀紧随其后。但好景不长,年,美伐他汀的厄运降临了,一直进展顺利的临床试验戛然而止了。
默沙东拨云见日尽管没有正式发表的研究报告,但来自三共制药的内部消息显示,在为期15周的动物安评试验中,长期服用高剂量美伐他汀的实验用狗患恶性肿瘤的比例升高。其实任何东西吃多了都可能会有问题,头疼腰酸等各种轻微的副作用,几乎每个药都有,关键是看它有多大的安全指数。[插图]即使是血压升高、肝功能异常等比较严重的副作用,只要它们是可逆的,即停药后可在短期内恢复正常,没有后遗症,还是可以在足够的安全指数下谨慎处理的。但是癌症就不一样了,首先它不可逆,其次它威胁生命。
假设长期服用剂量为每千克体重毫克时狗患癌症的比例增长了10%,你愿意冒这个风险吗?三共制药不愿意,药检机构也不可能批准通过,所以只能停止临床试验。
消息传到默沙东,化学结构上只多了一个甲基的洛伐他汀的开发也无法继续了,因为人们自然而然会推断:两者的化学结构和生物活性都如此相近,估计毒性也差不到哪里去。为了这件事,时任默沙东新药研究院主席、资深副总裁的瓦杰洛斯博士几次亲自前往日本,试图与三共制药联手,共享资源,共同研究美伐他汀的毒理,但是都被三共制药婉拒了。在默沙东内部,上上下下对他汀类药物的前景也不乐观。是整个他汀类药物出了问题,还是只有个别的他汀有问题?科研需要直觉,但更需要数据。直觉告诉我们,洛伐他汀很可能有类似于美伐他汀的毒性,但是我们必须拿出有说服力的数据。停止了临床试验后,默沙东又重新审定了洛伐他汀的安评结果,在继续进行长期和严格的毒性试验的同时,开始寻找结构上不同于这两个他汀的新型化合物。
值得庆幸的是,为期两年高剂量的动物毒性试验没有发现洛伐他汀有任何致癌的迹象,经各方专家的咨询和评审通过,洛伐他汀的临床试验于年底重新启动。数据结果显示,洛伐他汀对人体也是安全的,它说明了抑制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本身尽管在高剂量时也有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比如极少部分患者会出现肝功能的变化、肌肉的疼痛和痉挛等,但是不会致癌,美伐他汀的致癌性只是个例,就因为它缺了一个关键性的甲基。年,洛伐他汀经FDA批准成为第一个上市的他汀类药物,获得了巨大成功。
这个小小的甲基,不但挽救了洛伐他汀,也挽救了整个他汀类药物,使之成为历史上的“头号大药”——销售金额最大的处方药物,因为他汀类药物所面对的是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冠心病。
冠心病潜滋暗长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它的作用就好比是一个永不停息的泵,随着心肌的每次收缩将携带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血液经主动脉输送到全身,以供各器官和组织细胞代谢需要。那么,心脏自身的氧气和营养又如何得到呢?当然也是从心脏得到的。原来,在主动脉的根部分出了一条支脉,绕了一个小弯后回到心脏,那就是负责心脏本身供血的动脉,它的弯形如冠,所以被称为冠状动脉。由于脂质代谢不正常,血液中的脂质沉积在原本光滑的动脉内膜上,形成一些类似粥样物质的白色斑块,造成动脉的硬化和淤塞,称为动脉粥样硬化病变。这样的病变如果发生在冠状动脉里,那就成了冠状动脉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
因为冠状动脉的硬化和淤塞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也没有特征性的临床表现,所以早期诊断很困难,除非做高分辨率的心血管造影,否则不会被发现。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由于肢体功能的(正常)下降,大运动量的体力活动逐步减少,对心脏功能的要求也逐年降低,即使在心脏本身供血不足的情况下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起居。有不少病例显示,冠心病患者的冠状动脉淤塞高达90%以上,真可说已经是“命悬一线”,但仍然无明显特异性症状,偶发的胸闷气短被认为是正常衰老的一部分。
正因为如此,冠心病潜在的危险在没有提防的情况下不断地滋长。由于长期供血不足,冠心病患者的心肌已经变得很脆弱,承受力大大降低,一些原本习以为常的活动,比如挪动家具、排便、看紧张的球赛、喝酒、受惊吓等,都会在瞬间超出供血不足的心脏的负荷。
沉积在冠状动脉内壁上的粥样斑块大多数是稳定的,但是也有一些是不稳定的“易损斑块”,在心肌活动异常时这些易损斑块有可能会脱落下来,阻塞血管,引起心肌梗死,在很多情况下是致命的。
心梗的直接原因是动脉血管的老化和阻塞,而动脉血管老化和阻塞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之一就是高胆固醇。
舒降之打造经典在进行洛伐他汀临床试验的同时,默沙东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毫不放松,又找到了一个更加安全有效的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这便是后来的辛伐他汀(化合物3)。辛伐他汀与洛伐他汀的差别在于:又多了一个甲基。
有了美伐他汀的先例,人们自然会问:在洛伐他汀上加了一个甲基之后会不会引起一些新的副作用?所以辛伐他汀的药效和安评必须全部从头来过,不得有一点马虎。实验数据显示,辛伐他汀是一个功能强大的降胆固醇药物,最高可降低低密度脂蛋白(LDL)50%。其剂量为5~80毫克,对于高密度脂蛋白(HDL)及甘油三酯的水平没有实质性的影响。除了他汀类药物对极少数患者的一些常见的副作用外,辛伐他汀是一个安全且更有效的降胆固醇新药,于年底获得FDA的上市批文,中文商品名为“舒降之”(Zocor)。
他汀类药物能有效地降低人体血液里的游离胆固醇浓度,但游离胆固醇只是一个生物标记物(Biomarker)。魏尔啸年前的“胆固醇假说”能不能成立?他汀类药物到底能不能减少冠心病的发病率呢?年,默沙东公布了著名的“4S”临床研究结果,为他汀类药物的普遍应用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科学依据。
该临床研究项目的全称为“斯堪的纳维亚辛伐他汀存活率研究”(Scandinaviasimvastatinsurvivalstudy,简称4S),为期5年,跟踪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瑞典、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的冠心病患者共人。结果显示,服用辛伐他汀的患者血液里的游离胆固醇含量平均降低了35%,更重要的是,与对照组相比,可能的心梗死亡率降低了42%,首次为“胆固醇假说”提供了最直接的实验数据,成为冠心病临床研究领域里的经典。
基于“4S”临床研究结果,医学界普遍认为,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可以大大降低冠心病患者心梗或者脑梗的风险,延年益寿。中老年人即使未患冠心病,如果血液里游离胆固醇的浓度偏高,也应该服用他汀类药物,减少或延缓心血管的硬化和阻塞,提高生活质量。正因为如此,能有效抑制内源性胆固醇合成的他汀类降胆固醇药物很快成为历史上的“头号大药”,这一类药物的全球年销售总额高达数百亿美元。
一个小小的甲基,可以把美伐他汀打入冷宫;同样是一个小小的甲基,也可以使辛伐他汀(舒降之)成为预防和治疗冠心病的经典。遗憾的是,我们目前还无法预测,哪一个甲基(或是任何其他基团)会带来毒性或者副作用,哪一个甲基能提高安全系数或者药效。我们不能轻信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修饰和改动,安全评估报告可能要泼你一头冷水;我们也不能放弃几乎相同的衍生物,药效研究的结果也许会给你一个惊喜。我们必须用数据来说话。
益适纯一波四折不难想象,由于他汀的巨大成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降胆固醇药物的研究成了各大制药公司的热门。
同在新泽西州,距离默沙东实验室不远的先灵葆雅制药公司(9年被默沙东兼并)当然也不例外,他们锁定了冠心病研究领域的另一个热门靶点——乙酰辅酶A胆固醇酰基转移酶(Acyl—CoAcholesterolacyltransferase,简称ACAT)。
当时有文献报道认为,对ACAT的抑制能阻止胃肠道对外源性胆固醇的吸收,从而与抑制内源性胆固醇合成的他汀类药物起到互补的作用。先灵葆雅的ACAT抑制剂项目在启动后马上就遇到了麻烦。团队科研人员精心设计出来的在纸面上看起来很合理的新型化合物在一轮又一轮的生物测试中都没有呈现出预期的生物活性,令人失望。一个有心的实验员,把本来应该丢进废料桶的副产物分离纯化之后送去做了测试,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了。
这个产率不到5%的副产物不仅在体外生物测试中显示出了相当的活性,而且在高剂量的动物模型中也有一定的药效。如果说测试一个非设计的副产物已经是小概率事件,那么这个副产物不但有体外的生物活性,而且还有动物模型中的药效,就是小之又小的概率了。
先导化合物被意外地发现了。以这个有活性的副产物作为模板,研究人员接着一轮一轮地设计新的化合物,试图优化这个先导化合物。虽然这些新化合物对ACAT的抑制活性越来越高,但是在动物模型实验中的效果(胆固醇下降)不见有什么增强,停留在30%左右,远远低于适合临床开发的要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司高层慎重地评审了这个项目,认为该靶点与胆固醇的吸收没什么相关性,决定停止ACAT抑制剂项目,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其他更有希望的项目上。公司的决定是正确的,后来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ACAT与胆固醇的吸收确实没有必然的联系。辛辛苦苦做了几年的项目要下马,项目研究人员当然不高兴,他们所能做的便是将这个项目的实验数据整理成文,争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在整理这些数据和撰写论文时,研究人员经常需要补充少量化合物及其数据。于是,在部门领导点头之后,一名药物化学人员在项目被宣布下马之后又补做了2对(4个)新的化合物,打算在生物测试之后,将这些新的数据填写到论文的表格里去发表。尽管体外测试的结果跟预计的差不多,但在动物模型实验中意想不到的一幕又出现了:其中两个新化合物的药效比所有已知的化合物高出了很多倍。
新的突破口又一次被意外地发现了。在对这个意想不到的补充化合物进行代谢研究时,药理研究人员发现,该化合物所产生的药效可以持续很长时间,远远超过根据它的体内半衰期所预计的有效时间。也就是说,当血液里药物浓度下降至有效浓度以下时,它的药效却仍然存在。怎么会这样呢?经过研究人员追根溯源的仔细研究后,在用药后的仓鼠的胆管里发现了几个比药物本身活性更高的代谢产物。
在新药研发里,这样的好事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了这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发现,团队的科研人员通过化学修饰,合成出了体内活性比原先的临床候选药物高出倍的新化合物——益适纯(Zetia)。因为益适纯也只是在胃肠道和胆管里来回周转,只有很少量进入血液循环和身体的其他脏器,所以它的安全性也非常之好。
随着临床研究的顺利进行,公司开始着手准备向FDA报批申请材料,可是项目团队的研究人员又犯难了:益适纯所作用的体内生物靶标肯定不是当初立项时的ACAT,那到底是什么呢?在正常情况下,FDA一般是不会批准生物靶标未知的新药上市的,益适纯又是一个例外,因为它的临床前动物实验与临床试验的结果很有说服力,疗效显著,安全指数好,适应面广,与他汀类药物能起到很好的互补作用。后来先灵葆雅与默沙东合作研发益适纯与舒降之的复方制剂,在合作过程中,两个公司的联合研究团队也最终搞清楚了益适纯的生物靶标是PNC1L1——胃肠道里一个重要的胆固醇输送蛋白。
那是益适纯上市(2年)以后好几年的事了。
葆至能更上层楼如果说每一个成功的新药研发项目都包含着一点幸运的因素,那么益适纯的研发过程中幸运的因素就远远不止这一点点了。但仅仅靠撞大运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严谨的科学态度与实践,正因为如此,益适纯的研发团队不但歪打正着地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且还及时抓住了这些一闪即逝的机会,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成功。从机理上看,益适纯抑制胃肠道对外源性胆固醇的吸收,应该能与抑制内源性胆固醇合成的他汀类药物起到互补的作用,所以当益适纯还在临床试验阶段时,默沙东就拿着舒降之上门求合作去了。两种药物联合使用,最坏的可能性是出现药物相互作用(Drug-druginteraction),不但药效会受到影响,还有可能出现毒副作用;最常见的结果是既不互补也不互损,1加1等于2;最好的结果则是互补的协同效应(Synergisticeffect),出现1加1大于2的结果。
益适纯与舒降之联合使用的复方制剂葆至能(商品名Vytorin)就是这种最好的结果,非但没有相互干扰,而且还显示了很好的协同效应。科学是严格的。益适纯与舒降之联合使用可以有效地降低胆固醇,并不等于也一定能降低冠心病患者心梗的风险。换句话说,默沙东经典的4S研究结果并不能直接扩展到益适纯与舒降之的联合使用,只有进一步的临床研究才能说明问题,于是乎,又一个长达9年的临床试验开始了。
年,美国心脏协会公布了默沙东制药名为“IMPROVE—IT”的临床试验结果,数据显示,舒降之与益适纯的复合制剂葆至能可显著减少高危冠心病患者的心血管事件。益适纯与舒降之的互补性使得葆至能非常适用于对他汀类药物敏感度较低的患者,只要用相对较低的剂量就能将他们血液里的胆固醇控制在健康的水平。
葆至能可以同时抑制胆固醇的内源性合成与外源性吸收,在高胆固醇和冠心病的治疗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比例已经逐步上升到接近50%,在同一时期内,这个年龄组的心脏病死亡率持续显著下降。[插图]可能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吸烟人口的下降,饮食更为健康(至少在某些方面),心脏病治疗的改善,心梗紧急治疗更为及时,等等。尽管我们很难把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效果一一区分开来,但是毫无疑问,服用他汀类药物所带来的整体人群的胆固醇水平降低一定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文章来源:梁贵柏《新药的故事》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jiajiasport.net/gxbzl/11241.html
- 没有推荐文章
- 没有热点文章